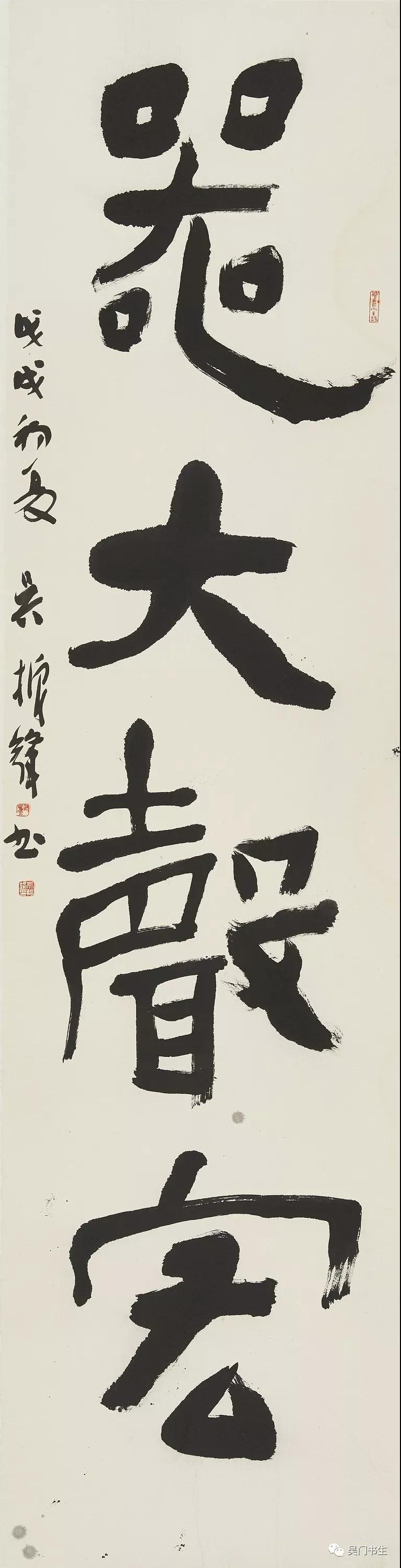
木心先生有首詩《從前慢》,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你鎖了/人家就懂了。"木心詼諧,我讀懂他的一層意思,從前的鎖是美的,好看的,是鎖君子不鎖小人的。鎖,就是一個樣子,你鎖了,別人就懂了,主人不在,不可造次,反而是安全的。
在我童年的家鄉,屋門常常是不鎖的,有時空掛著一把銅鎖,也只是“樣子"。其實,“樣子"就是規矩。誰要是借件急用的家具,非得進門不可,也可以拿走,一般都會找個鄰人為證,事后要帶上禮物答謝的。鎖,實際上就是一條規矩,一道法令,沒有人輕易踐踏的。 進城后,住上樓房,先是有了暗鎖,我常帶一串鑰匙在身上,很不方便。再后來,又裝上了防盜門,目的是防賊,實際上成了自己的枷鎖。好幾次,忘了鑰匙在家里,少不了的折騰。我的一個堂兄,是位醫生,住一樓。樓上家家都安上防盜門,他卻偏偏不安。他說,安了,若遭賊惦記,也等于沒安。反而,若有個病人找你,多費時間。那年冬天,有小偷把樓上每一家都光顧到了,卻給他家門上留了個條子。上面寫著:“你不防我,我也不擾你。好人過個好年吧"。第二天一早,我的這位哥看見后弄得哭笑不得。記得賈平凹當年寫過他的“靜虛村",說是箱柜的鎖最好空掛著,賊拿走了東西,箱柜仍是完好的。意思差不多。如今,到了智能時代,用的是指紋鎖,甚至是刷臉就能開門,不知道鎖還會演變出什么花樣。
我想到老先人用過的“封泥"。在漢代,文書送達都要封印。因為文書是寫在竹木簡上的,所以一般不直接蓋印在文書上,也不捺印在木簡上。封印有兩種,一種是把捆扎好的竹簡放在袋子里,將一個一寸見方的木框附于袋口,再將系袋口的紐帶的兩頭纏在木框上,在木框上填入膠泥,趁膠泥不甚干時即蓋上印章。還要把“某某之印”等印章上的文字抄寫到收件者簡札的表面或文書袋上。接收方確認印文與附注文字相同后才可以開封。膠泥塊是證明文書送達的標志,是不能拆毀的。另一種是,在厚厚的木簡上預留嵌膠泥塊的楔孔,上邊刻著系紐帶的凹槽,捆扎成束后再蓋上封檢印。這種封檢印的干膠泥塊,在地下沉睡了兩千多年,我們叫它“封泥"。這是印刷術的先聲,想必也有鎖的功能吧。如今,偶爾也能見到“鉛封"的遺跡,那便是先前的封泥,抑或是“鎖”。
人心其實是最難開的鎖。人往往活在自己設置的有形無形的網中,人成為自己內心的囚犯。人要從心囚中出走,打開這把鎖的鑰匙有兩把,一是灑脫的心性,一是勇氣。但愿,鎖,只是樣子。
2018,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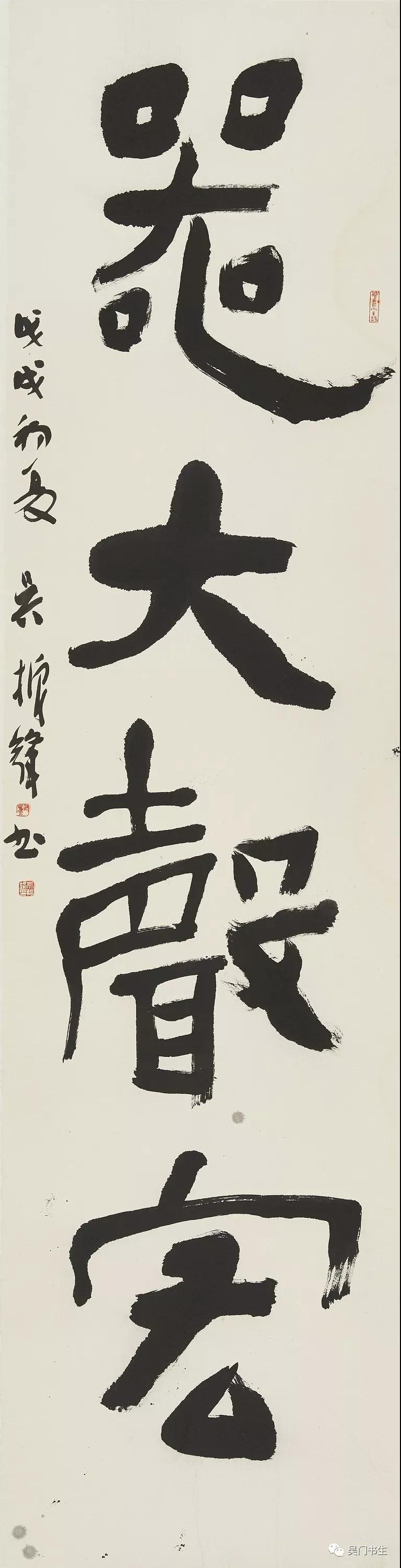





 位客人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