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0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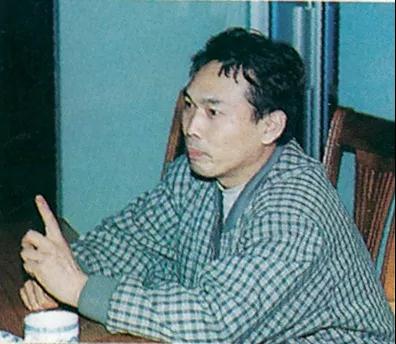
改革開放40年:小小說人物(14)
蘆芙葒的文體意識
程 華
小小說也稱精短小說,作為文學敘事的一種類型,是在篇幅上有限制的敘事藝術。其實,不論哪種文學藝術,作為獨立的審美創造形式,在結構、敘事或精神旨趣等方面都有來自文體特征上的限制。“每一種文體 ,一旦獲得了名稱 ,它就具有某種獨立性,能夠顯示某種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殊性東西。”[1]如果說“詩歌文體”追求的是“詩性話語”,受歌唱、抒情等表達方式的限制;小說文體屬于敘事話語類型,強調對可能性事實的敘述。小說敘事的歷史發展和文類形式復雜多樣,僅從篇幅的限制上來劃分,就有長篇、中篇、短篇、精短小說之稱,以往人們總是將精短小說和短篇小說并為一體,但從文體的限制性方面來看,精短小說和短篇小說在結構模式、敘事模式和精神旨趣上所體現的特點是不同的。短篇敘事中所追求的完整情節或典型人物在精短小說中是不可能實現的;精短小說中可提供的以小見大、精妙幽微的敘事旨趣也是中短篇小說無法達到的。我更贊成汪曾祺老先生對小小說文體的界定,“小小說自成一體,別是一功,如斗方、冊頁和扇面兒”。[2]近幾年,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創作隊伍的壯大,各類媒體雜志的推廣,精短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形式越來越受到讀者和評論家們的青睞。
當然,精短小說的創作者們也在不斷地探索和發展小小說的文體表現形式。小小說原本是民族文學的產物,如中國早期的神話、六朝志怪、筆記體小說、短篇傳奇以及蒲松齡關于狐妖的小說,其篇幅都是很短的,且有現代精短小說可資借鑒的藝術手法。但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精短小說的引入,特別是對以歐·亨利等為代表的精短小說家的推崇,諸如“偶然性情節加出人意料的結局”的敘事模式一度成為精短小說敘事藝術的追求,“情節的巧合”避免了故事的完整性敘事,“結尾的出人意料”也能體現作者對生活思考的能力,非常適合精短小說緊湊短小的情節和篇幅。但是,敘事模式的單一化,也會禁錮和妨礙小小說文類的發展。
如何在限制中求突破,在拘束中求自由,這也是小小說作者面對的問題。具體說來,如何在小的篇幅中發揮敘事的自由,怎樣超越現實事件而進入到藝術的構思和講述中,小小說文體對作者敘事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寫作者有自覺的文體意識,而擁有自覺文體意識的作家,思考怎樣敘事比敘述什么樣的故事更重要,思考如何在較短的篇幅限制中讓故事和事件升華,以及運用什么樣的表現形式對生活進行藝術的濃縮?如何把對生活的態度和人生的理解通過隱喻和哲理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小說寫作者在創作構思中,要把對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形象化到具體的藝術結構和藝術形式中,借助“精短的意蘊結構, 精短的情節結構和精短的句群結構”[3]來進行小小說創作,自覺形成小小說的文體意識。
文體意識的自覺是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來完成的,需要堅持不懈的對文體的有意識的實驗和探索。蘆芙葒在小小說創作領域是起步較早的作家。1995年就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只鳥》,其后的《收音機》《飛向空中的盆子》《麥垛》《三叔》《裊裊升起的炊煙》《一只叫毛毛的狗》《父親的電話》等,都表現出作者有意識的經營小小說文體。其文體意識的自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他把對生活的思考進行藝術的抽象,提煉成富有象征意味的藝術形象,形成精煉豐富的意蘊內涵。其次,突破“巧構”性的情節,重視敘事結構的營造,把對生活的理解和體會通過小說敘事過程傳達出來,而非僅僅進行情節巧合的安排。三是具有獨特的精短小說的留白的藝術。
一、蘊含豐富的藝術抽象
關于精短小說的寫作,蘆芙葒曾說過,“熟悉的生活,陌生化的小小說”,[4]從熟悉的生活到陌生化的小小說,在蘆芙葒這里,其實是藝術的抽象過程。高行健說:“藝術的抽象側重于抽象思維的方式,它注重的不是具體的、感性的外在形象,而是內在的精神活動,在藝術創作中,直接訴諸理性、精神和觀念。它是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方法的補充。深刻的思想一旦獲得了形象,組織到戲劇沖突之中,得到藝術上強有力的體現,也一樣成為不朽之作。”[5]凡經過藝術抽象的作品,都是作者長時期對生活進行理性思考的作品,作者抽象出來的藝術形象,其實是形象化的生活哲理或人生思考的體現,而不僅僅是指某一典型形象。蘆芙葒善于借助藝術的抽象從熟悉的生活中提煉藝術形象,不過,蘆芙葒在藝術抽象中并未走向極端或先鋒實驗的結果,他將他對生活的思考提煉出一個藝術形象,并借助文學藝術結構使之體現出來。在蘆芙葒的小說中,他的思考和思想都獲得了具體的形象,而這些具體的形象一定意義上又成為他結構小說的線索,這樣,藝術形象借助小說敘事結構,就獲得了鮮明而獨特的藝術效果。
《水鬼》是蘆芙葒早期的小說,雖說在藝術的營構上沒有他后來的成名作《一只鳥》蘊含豐富,但也表現出作者高超的藝術抽象能力。《水鬼》圍繞水鬼說話、人不信鬼話、鬼話靈驗等情景,提煉出一個水鬼的形象。這個故事講下來,不僅作者不明白,鬼為什么要幫助人?讀者也不明白?可世上的事又有多少是我們能明白的呢?小說原本就是想象,水鬼就是作者美好的一個想象,關鍵是這個想象有情理的基礎,比如水鬼長得和人一樣,并不使人憎;水鬼知道人間之事,水鬼的鬼話并不是糊弄人的鬼話,是真話,敘事者我的家就是因為缺木料而蓋不起房;水鬼的鬼話里也有道理,夏天的山道,常發大水,大水漂來木料和門窗也是常有的事,這常有的事不就是我們一般人希望的奇跡嗎?我們相信奇跡,也可以相信鬼話。這個小說的敘事魅力就在于通過超越現實的想象說明,在這世上的好多事,人不幫,就有鬼來幫;在人那里找不到的因緣,在鬼那里就有來由;有一個現實的世界,也有一個鬼的世界,鬼的世界是幻想的世界,也是作者將真善美寄予于此的世界。
在奇幻的想象里凝練藝術形象,除了《水鬼》,還有《活寶》。“活寶”是敘事的線索,也是藝術的抽象。小雞變金子,這是民間的活寶,可是當人們篤信天上掉餡餅的事時,活寶就不僅僅是餡餅了,其實就成了一種欲望,尋找活寶的過程,也就成了欲望實現的動力。貓頭爸爸發現逮在手里的小雞變成金光閃閃的金塊時,他就相信有活寶。可活寶在人們傳看時,掉在地上消失了,于是就有了貓頭一家拼命的尋找活寶的行動。奇幻的想象一旦和現實聯系起來來,就有了諷喻現實的功能。結尾是典型的微型小說的結尾。“一個金光閃閃的東西在地上一跳一跳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撲了過去”,[4]那是他們心里的欲望的映現。其實,在現實的世界里,并不只有貓頭家渴望掘到金寶,村子里的人們和他們一樣,大家都做著尋找活寶的夢,比如淘金行為。這樣,活寶是想象的,淘金是現實的,兩廂對照,也是藝術的襯托和呼應。
借助奇幻的想象進行藝術抽象表達作者對人生和生活的思考,在現實世界進行藝術的抽象,其所提供的不僅僅有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思考,還有生活景象和時代映像,其背后是廣闊的生活畫面和時代背景。《一只鳥》是蘆芙葒的成名作,《一只鳥》中的這只鳥,也不單單是普通的鳴叫著的鳥,鳥聯系著三個人的人生命運和心理世界。這原本是盲眼老頭的鳥,他的兒子阿捷冤死,他買了這只鳥,并取名為阿捷,是為思念兒子,鳥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兒子阿捷的化身。退休的法官看到這只鳥,并千方百計得到這只鳥,是因為他在斷案中,曾冤死了一個叫阿捷的青年,他從盲眼老人那里得到這只鳥,并放了它,是為了釋放他內心的悔恨。一只鳥的背后,是如此豐富復雜的人事糾葛和人生故事。現實的三個人的人生故事錯綜復雜,完全是長篇小說的篇幅,作者通過提煉“一只鳥”這個形象,把聯系三個人的關節點找出來,在“一只鳥”上表達出每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背后的生活世界,這是藝術抽象的魅力,它不僅考驗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能力,還考驗著作者的藝術構思能力。在具體的敘述中,作者緊密圍繞一只鳥展開敘事,一只鳥既是藝術形象的抽象,也是敘事線索。這樣,繁瑣的生活事件就被作者編織到線索清楚的藝術敘述中,獲得了不一樣的藝術體驗。
《裊裊升起的炊煙》中一個煙囪一縷炊煙,一縷炊煙就是一戶人家,一家煙囪通了,家里就有煙火氣,一村子煙囪通了,村子里也就有煙火氣。不過,作者在這里將煙囪冒煙與家和人興聯系起來,表面上說的是煙囪冒煙,其實說的是家和人興。“裊裊升起的炊煙”是家和人興的形象隱喻,家的諧和才會有村子的和諧,村莊的和諧也才會有國家的和諧,再往寬里說,就是傳統的修身齊家的修德理念。從一個煙囪到傳統道德,這中間是藝術的提煉,也是對生活理性思考的結果。
如果說《裊裊升起的炊煙》描述的是相對和諧的農耕時代的生活圖景,那么,《麥垛》的背景則是城鎮化背景下的打工人群的生活現實。“麥垛”也是經過作者理性思考后抽象的藝術形象。城鎮郊區的這個“麥垛”,和“一只鳥”,或和“裊裊升起的炊煙”一樣,既是藝術形象,也是敘事線索。麥垛一方面聯系著男人的情感,隨著城市化的擴大,麥垛里有他對農村生活的依戀,作者通過敘述男人對麥垛的依戀來表達的;一方面聯系著打工夫婦的夜生活。來城里打工的年輕夫妻,住不起高昂的賓館和酒店,只有在城郊的麥垛里過夫妻生活,麥垛是見證農村打工夫婦的貧窮。小說結尾,原本要賣掉的麥垛最后被留下來,也留下了作者對這大時代下農民生存現狀的思考:城市化發展是必然趨勢,失去麥地的人們,不論是遠離麥地的打工夫婦,還是逐漸失去麥地的城郊農民,他們不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在身體上,還能依賴麥垛多久?
精短小說先天的限制在于沒有太大的篇幅,如何在局限的篇幅中表現有深昧的意蘊,藝術的抽象是非常重要的。蘆芙葒作品中的“水鬼”“活寶”“一只鳥”“麥垛”“裊裊升起的炊煙”,還有“遙控器”“收音機”等藝術形象,之所以說它是藝術抽象的結晶,在于這些形象背后有作者對生活的思考,是作者長期理性思考后提煉的形象,這些形象和小說結構結合,被組織在敘事過程中,既是作者精神思考的表現,又是藝術結構的線索,表現出作者獨特的創造性。
二、突破“巧構”性的情節,重視敘事結構的營造
為了縮短敘事的過程,“懸念”“巧合”是敘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敘事因素。但生活中未必處處是巧合,且巧合往往給人炫技的因素。小說來源于生活,凡是生活的豐富、復雜,也可以出現在小小說的創作過程中。若能有警醒的意識,突破情節的因果關系和“巧構”的情節關系,在小小說的敘事中,無疑具有變革的意義,其實也表明作者生活態度以及對小說藝術的全新的思考。蘆芙葒比較重視如何講述故事,很多時候,不是通過設置“情節的巧合”來講故事,而是讓生活中的事件自然地呈現出來。
蘆芙葒早期的作品里也有巧構性情節,比如《歡迎光臨》,一對男女固定在某公車站牌下約會,對面三樓的窗戶下可以看見“歡迎光臨”的牌子。“歡迎光臨”也是敘事線索,這個線索有非常鮮明的巧合因素。“歡迎光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她說,這個牌子有意思,除了歡迎光臨,什么信息也沒提供;接下來他們幽會,他很想讓她光臨自己的家,可她一次也沒提出來光臨他家,她可以光臨任何地方,卻從未光臨過他的家,他死了,她才發現,“歡迎光臨”從一開始就在那,是他寫給她的,可是人死了,這光臨又有什么意思呢?故事情節的背后是人生的感慨與無奈。
這樣的敘事類似歐·亨利的小說結構,通過設置偶然性情節,以及出人意料的結局,來揭示生活現象和人生哲理。這種情節之所以成為一種類型或模式,也是因為生活中本來充滿偶然力量,而且,出人意料的結尾又能最大限度的表達對生活的哲理性體悟。比如蘆芙葒《死亡體驗》中一對男女本來已經下定決心結束生命,可是就在他們最后完成他們人生最快樂的男女體驗之后,準備沉潭之時,村子里二炮的花炮房炸了,人們喊叫著救命,村子里的狗的叫聲和人喊叫的聲音使兩個人體悟到,“沒有想到,他們為了死而絞盡腦汁,卻還活著。而那些快樂地活著,并想永遠活下去的人,卻遭了不測風云。”[4]于是,他們解掉綁在他們身上的石頭,走回到村子里。花炮作坊的被炸具有偶然性,而這一偶然性情節在這里的用以是使主人公明白了關乎生死的人生道理,這是具有巧構性的結構設置。
小說的邏輯與生活的邏輯不同,王安憶認為,小說中的邏輯是作者藝術化營構的邏輯結構,若能以最小的因獲得最大的果,且能給人以啟示,就是好的小說。情節的巧合簡化了生活事件的發展,是快速達至結果的方式,一定意義上,有簡化生活的印記。突破情節的巧合,也就是突破巧構性邏輯,把對生活的理解自然地通過敘事呈現出來,在蘆芙葒后來的小說中,表現比較突出。
《飛向空中的盆子》在我看來,就具有現代主義敘事的魅力。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孩童的限知敘事視角,敘述的是我六歲時發生的一個故事。在我眼中,那時九歲的小伍子總有稀奇古怪的想法,他作雷管,將雷管放到了木盆下,要我坐到木盆下,我不坐;這時候梅朵搖搖擺擺來了,梅朵四歲左右,小伍子讓梅朵坐在木盆下;我看梅朵坐,我也要坐,我和梅朵都坐在木盆下,然后小伍子就點燃了接著雷管的導火線。我還聞到了導火線放出的很好聞的氣味,我們都很高興,過了一會兒,村邊響起一個驚天動地的聲音,人們都跑去看看熱鬧,小伍子也去了,我和梅朵也去看熱鬧了,木盆下的雷管爆炸了,“我們回過頭,就看見我和梅朵兒剛剛坐過的那只木盆在一片煙霧中,就像是只笨鳥一樣飛向了藍天。”[4]這個故事看似平平常常的講述,卻有驚動人心的力量。看到結尾,不禁感嘆,幸虧飛向空中的只是盆子,而不是我和梅朵。災難無處不在,一個奇幻的想法會制造災難,一個偶然的聲音也會避免一場災難。
這篇小說的魅力在于,不是通過作者設置種種巧合來體現生活中處處充滿偶然的事件,而是通過敘事過程實現的。第一人稱的限知敘事傳遞給讀者的是真實的感受;童真的視角又使故事講述過程自然有序;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力圖呈現事件本身的面貌,有點類似海明威的冷靜簡潔的“冰山”敘事,作者沒有對事件進行相關的哲理性評價,或如《死亡體驗》一般,借助主人公的體悟對事件進行評價。這種純粹客觀的敘事,突出事件本身的偶然、無序以及不確定性,偶然性的事件是不為我的思想所掌控的,這樣,看似是事件本身的發展,背后是敘事者對生活的態度和理解。不僅如此,這樣的凸顯事件本身的發展,一方面隱匿了作者的態度,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參與其中,考驗的是作者和讀者的雙向的思考能力,彰顯的是敘事本身的力量。
為了強化敘事的真實可信,作者在敘述三個孩童游戲的過程中,通過變化敘事視角,增強敘事的現場感和可視性,可視性是一種藝術效果,作者講述故事的過程,讀者如同身臨其境。比如:
他對梅朵兒說,嗨!你走了這長時間的路,累不累?梅朵兒就點了點頭。小伍子說,我就知道你累,給你準備了一只木盆。現在你就坐在這只木盆上歇歇吧。[4]
這里以小伍子的視角敘事,如果用我的視角,則是小伍子給梅朵準備了一只木盆,讓她坐上去,敘事就會很生硬,沒有如臨現場的透明感,同時,通過變化視角,對孩子的心理把握比較客觀,白描化的語言,使小孩的形象充滿童趣。
“小伍子的臉上當下就爬滿了陽光”“梅朵兒可高興了,她坐在了那只木盆的上面,臉就像是一朵向日葵一樣看著我們笑。”[4]
這種現場感強烈的敘事過程,也凸顯了生活中處處充滿了偶然,這是通過敘事過程體現現實生活有很多令人猝不及防的事,當然也有許多無法避免的災難,作者不是設置巧構性情節完成對生活的思考,而是將生活過程呈現出來,其通過敘事所呈現的生活的面貌比設置巧構性情節呈現對生活的思考更具有穿透生活的力量。
重視敘事體驗的作者,其情感態度往往在敘事語言的后面。比如《梅朵兒》中,結尾是這樣寫的:“每次,梅朵兒站在木匠兒子的墳前時都會想,如果這個人不死的話,如果我要是嫁給他的話,那現在的生活又會是怎樣一個樣子呢?”[4]作者在整個敘事過程中,通過事件和細節敘述木匠是個善良的人,木匠愛梅朵,木匠很孝順;相反,鎖子砍死了木匠,鎖子很善于掩飾,鎖子無愧疚。若從敘事背后的情感看,木匠是更被敘事者中意也更善良的人,所以,結尾的敘述就余味無窮,如果梅朵先喜歡上的是木匠呢?事情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這里也有生命中的偶然性因素的體悟,但這些,都不是通過情節設置,而是在一點一點的敘事中體現出來的。
《牙齒》中,敘述了三件事,一是我掉了一顆牙齒,我墊著凳子將牙齒扔到了房檐上,我以為我扔到了房檐上,因為我沒聽到牙齒滾下房檐的咕嚕嚕的聲音;二是小寡婦與楊二嫂在爭吵撕鬧,楊二嫂的婆婆喜歡吃小寡婦的豆腐腦,老太太的豆腐腦碗里突然出現了一個牙齒,這個牙齒不是老太太的,小寡婦也不知道牙齒從哪里來的,楊二嫂認為牙齒是小寡婦的,于是兩人撕扯不斷;三是小寡婦的豆腐腦后來幾乎沒人吃了。三件事,從敘事過程看,我掉了一顆牙齒與小寡婦的豆腐腦生意八竿子打不著,但真的就沒關系嗎?誰也說不清,這就是敘事的魅力,無因有果的事情,在小說里是靠敘事成就的。在現實生活中,矛盾有時候確實沒有所謂的因果,這是生活的道理,將生活的道理借助敘事呈現出來,讓讀者感受生活的復雜,這就是更為現代的敘事方法。
與《牙齒》相似的敘事手法,在《懷表》中也體現出來。《懷表》中懷表與寡婦兒子的死又有什么關系?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要說沒有關系,可如果懷表未被借走,寡婦的兒子可能不會死。這個故事也是說明悲劇并不一定都有因果。在這個故事的敘事過程中,凸顯偶然因素對人的命運的影響。一般情況下,人打獵物,可是在這里,卻是獵物打了人。蛇按動扳機,子彈恰好從裝懷表的地方射出去,悲劇發生了。不論《牙齒》,或是《懷表》,在情節上都有打破巧構性的情節設置的敘事因素,因為巧構性情節擺脫不了因果關系。把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借助現代敘事結構呈現出來,完成對生活和生命的偶然性體驗,是蘆芙葒在小小說中發覺的敘事的魅力。
小說里,題目有時候并不是主題的提煉,而是結構線索,是藝術的抽象。藝術抽象和小說的敘事結構以及行文布局結合起來,既是作者對生活的藝術的提煉,又關乎作者對文學的認識和對生活的態度。《收音機》中,鄉村里淳樸的人情,或者人性中細微之處,也是通過敘事來呈現的。作者越是鋪敘胡孩兒癡迷于鼓搗收音機,越是讓人想象他對家庭的疏落與遺忘。因而,當故事的關口出現,收音機制造出來了,家庭也消散了,如果沒有前面大篇幅敘寫胡孩兒對收音機的癡迷,那么當第三次他將人們召集起來展示他的收音機時,他老婆和情人出現在收音機里的聲音就有些橫空出現的因素。因此,作者最后補敘胡孩兒離開時對情敵家的天線的修理和穩固,這一方面是人情的展示,胡孩兒非有多大的情懷才能做到,另一方面也是主人公對自我的反省,人情和人性美是在敘事中自然地得到體現。《一條叫毛毛的狗》中,小寡婦家的毛毛狗不叫了,因為它把劉醫生當作了自己家里人;小寡婦家的毛毛又叫了,是因為它恨劉醫生殺死了自己的兒子。毛毛叫與不叫,背后是人情與人性。《狼吃娃》中“狼吃娃”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游戲,比如我與孩子們的較量,孩子們驅趕我,我在樹上對著他們撒尿,誰贏誰輸呢?那只是游戲。但在大人的世界里就不一樣了。我母親和狗娃偷情,如果被我父親撞見,那就真成狼吃掉娃了,為了防止狼吃娃,所以我就用土塊給我母親他們提個醒。“狼吃娃”是作者提煉的藝術形象。狼能否吃掉娃,在于娃的防范能力。父親能否發現母親的偷情,在于我能不能給母親暗示。而我能不能給予暗示和防范,則意味著一個家庭的災難與悲劇。所以這個大樹、大樹上的我等,包括我和孩子們的游戲等都是敘事的鋪墊。故事的寓意全在敘事中。
文學敘事的力量不僅僅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將更多的敘事元素進行巧妙組合,表達作者對生活、對人情人性的更深層的理解。突破情節的巧合,重視敘事因素的呈現,其實是現代主義小說敘事的理念。現代主義小說重視敘事結構的安排,而非情節的因果關系。這樣,不僅作者借助敘事成就了他對生活的理解,讀者也能參與其中,通過作品故事完成對生活的思考。蘆芙葒突破情節的巧合,注重借助敘事元素呈現事件的整個過程,完成對生活和生命的偶然性體驗,是蘆芙葒在小小說中發覺的敘事的魅力。同時,當作者重視如何敘事比敘述什么樣的故事更重要時,這也體現出作者強烈的敘事意識和文體自覺。
三、重視留白的筆墨情趣
留白,如果用在整體布局里,它就是一種結構方法;如果把留白作為表現手法,往往給人回味無窮的詩意表現。留白在文學寫作中,要通過語言表現,也可以成為一種筆墨情趣,表現作者在語言表現方面的特點。
凡講到小小說藝術的,都會講到留白。小小說鑒于篇幅的限制,很難將故事講完整,在結構布局上,它要略去細枝末節,甚或前因后果,單將最能體現作者意旨的地方講明白,這是結構上的留白。比如蘆芙葒的《扳著指頭數到十》,這是一篇寫親情的文章,第一人稱的孩童敘事視角,在視角上與《飛向空中的盆子》相似,給人真實感。三個人物,都有故事,但作者重點只講述我的故事,在我扳著指頭只能數到十的年齡,爹爹老出去,我等爹爹回來的辦法是用土捏小狗,在我捏了五個十零三個小狗的時候,爹回來了。娘和爹都說我計數記錯了,娘也不識字,她攢積蛋,攢了三個十零三個;不僅如此,爹爹記憶天數的方式是掰饃塊,他掰了三個十零四塊。同樣的天數,數出不同的數,就是個人心情的體現。孩子愛父親、又嘴饞的孩童天性被表露無遺,同時,一家三口親密相愛的情感躍然紙上。敘事者將我捏小狗寫的很仔細,我是偷拿別人的泥胚,因為我說要捏小狗,娘就允許了;中間我希望爹爹快點回來,一天捏兩個,被娘識破,我覺得日子過得很慢。娘攢雞蛋、爹藏饅頭里其實有和我一樣親情,但作者在最后才寫出來,中間略掉的,其實就是留白。留白用得好,不僅使文章結構簡潔清晰,還能強化敘事的蘊含。比如,僅只捏小狗就足以打動人,還有數雞蛋和攢饅頭,既凸顯了每個人愛家人的方式不一樣,人都從自己的性情出發表達著對家人的愛,這愛的因素疊加起來,更能打動人。
汪曾祺老先生說,小小說作為文體,介于詩與小說中間,他非常推崇留白在小說中的作用,可以增加一些回味。把留白作為一種表現手法,可以強化作品的詩意。蘆芙葒的《小麥》,講述的是外來務工者艱難的城市生活,從敘述中得知馬勺愛小麥,小麥也愛馬勺,可小麥最后卻走了,馬勺“不明白小麥怎么說走就走了”“他打開昨天晚上沒有打開的那扇門。房子里是一張雙人床,兩套睡衣整齊地擺放在枕頭邊。”雙人床上的兩套睡衣就是留有余味的點睛之筆,小麥和馬勺的結局以及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局,就全在這留有余味的細節之中。在這個故事中,愛情是精神生活,現實生活卻擺不上臺面,那雙人床上的衣服那么扎眼又那么空虛還有一絲無奈。
蘆芙葒的小說素材多源于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凝練詩意的想象可能比虛構的故事更艱難。《守望》中的小油匠死得蹊蹺,人們想象小油匠是被狐貍精纏死的,因為村子偏僻又貧窮,年輕的后生們都娶不下媳婦,能被狐貍精纏著也是有幸。這本是當笑話和想象的故事講的,沒想到,長武卻聽信了這個故事,“長武穿著平素很少穿的那套干凈衣服,坐在小油匠的那張床上,正癡癡地望著窗外的桃林發呆呢。”長武守望的姿態,給讀者留下無盡的想象和回味。小油匠在守望中死去,長武又會怎樣呢?這既是結構上的留白,也是詩意的想象。光棍們生存悲劇的背后也暴露出光棍村的現狀。
《三叔》可作為精短小說里的經典,八百多字的篇幅中,寫進了人性的復雜與豐富,其藝術的魅力,在于從結構到表現手法再到語言的整體的留白藝術。從結構上看,文章主要圍繞三叔的心情變化線索寫的。三叔養雞場,家旺是村長,三叔總舉著一枚雞蛋查看蛋黃是單黃還是雙黃,三叔和家旺一為龍一為虎已經斗爭了多年,蛋的雙黃與單黃在這里有喻指,一村不容二虎,一蛋殼不容雙黃;三叔研究蛋黃的當兒,二皮子報告三叔家旺的兒子翻車了,住院了,雞蛋就裂到地上碎了,這是鋪墊,按理說,這時可以確信單黃蛋了,也就像三叔想的,家旺家倒了霉運,他真的就變成村子里的青魚,而家旺在三叔面前,像一條死魚樣再也翻不起身;家旺消沉了,三叔也打不起精神,于是三叔借錢給家旺,希望家旺振作,三叔希望家旺振作,實際上是希望日子過到以前,有人和他斗一斗。失去對手的日子,對于三叔來說,也是難熬的。從結構上來講,它只截取的是人心理的一個片段,至于三叔和家旺如何斗,三叔和家旺是什么性格的人等等,作者都略去不寫,省去事件而專注心理,這是結構上的省略。從表現手法而言,文中用意味深沉的意象,來豐富人物的心理,比如“三叔昂首挺胸地站在一群母雞們中間,手里握著拳頭大一枚雞蛋。因此,每當太陽出來時,他總會瞇縫著眼,對著太陽舉起那枚雞蛋。他一直想弄清這個雞蛋是雙黃還是單黃。”此句可知曉三叔的性格,他不服輸,內心里有昂揚的斗志,而這斗志是家旺給他的。當三叔聽到家旺家翻車后,一句“雞蛋碎了”,也給人留有余味。一是這件事對三叔來說,確實意想不到,二是此句與后面三叔和家旺都提不起精神,是互為映照的,一個事件,傷害的是兩個人。借意象來暗指人的心理以及事件的發展和結局,給人意味無窮的想象。整篇文章,雖只有867個字,但卻是無一字多余,多一字也無益,寫出了人物非常復雜、跌宕起伏的心理變化。此篇文章用出色的藝術表現,既能看出人的個體心理的發展,也寫出了普遍的人性變化。人的好斗心理與人的孤獨狀態的互為辯證的關系。
結語
現代社會的發展,掌上速讀時代的來臨,精短小說比起中長篇小說逐漸成為普通大眾的寵兒,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精短小說的創作;同時,我們也看到,精短小說創作領域也普遍存在功利化寫作傾向,或捕捉社會上奇聞異事,以博取大眾的眼球和閱讀量;或進行模式化和類型化創作,制造千篇一律的小說體式;或是對事件進行堆積而缺少藝術的選擇,凡此等等,精短小說在這個不斷趨向功利化的時代,對生活思考的能力被淹沒在快速化的社會發展中,對藝術的追求又被功利化的需求所替代。同其他文類一樣,在精短小說創作領域,我們也需要那些對生活進行深度思考的作家,呼喚那些將精短小說作為獨立文體,自覺探索小說創作藝術的作品,從這個角度來看,蘆芙葒的精短小說創作,在這個時代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李詠吟.文體意識與想象定勢[J].文藝評論,2014(2):10-20.
[2]汪曾祺.小小說是什么[J].小小說,1987(3):42-45.
[3]王曉峰.小說精神與小小說文體現實[N].文藝報,2002.11.26.
[4]蘆芙葒.一條叫毛毛的狗[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5]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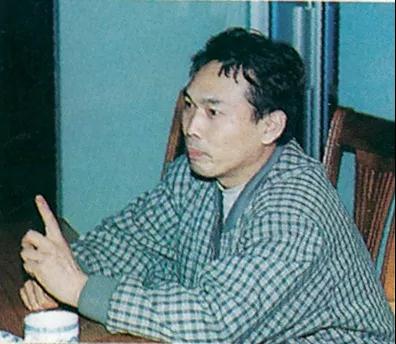





 位客人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