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古槐市
文\田華

丙申冬,仲月,天氣尚好,太陽暖暖的。約十時許,我說,今兒應(yīng)該去尋訪古槐市的。
古槐市,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地名,一代著名廉吏楊震老先生曾經(jīng)在那里設(shè)館講學。因那里多槐,每遇陽光照射,眾槐即蔽日遮天。時,楊震門下學子眾多,號生員三千。故得“關(guān)西夫子”之名也。
既有生員聽講、求學,自然,服務(wù)業(yè)也水起風生了。地方志載,當時的商事甚是繁華。故而人多成市。曰,槐市。
古槐市,乃遠古先賢傳授儒家學說、華夏民族文化之道德精髓的地方。我須懷著崇敬之心而去,于是,隨洗了手臉,以示對古賢達的敬畏。
古槐市在華山峪以東,相去之距約1.5華里,名叫牛心峪。
牛心峪就在我家樓的后邊,步行,亦不過四十多分鐘的行程。那天,雪駐不過幾日,加之,道路常年少有人行走,路兩邊荊棘叢生,蒿草像要把那逶迤的小路遮覆了去,為了行走方便,途中我于路邊樹上,攀折了一枝木棍在手,把伸向小路上的荊棘蒿草撩撥了開去,才小心又吃力的向上攀爬而去,這樣的走法,真可謂是手足并用了呢。
盡管說這路難行,而真正難行的,是過了鐵路往山上爬行的那段。
山上的路,彎彎曲曲的,一如羊腸,加上雪未消融凈盡,沿途的殘雪,斑剝出一片兒一坨兒來。由鐵路處到峪盡處,全程不足四百余米,可卻讓人大汗淋漓;幾次腳下打滑,差點兒跌倒,幸虧了那根棍子,成了我的另一條腿。
按照之前文管所同志介紹的情況判斷,謝天謝地,我終于尋找到了——古槐市。
這是一箕狀的猶如心形的山谷。
谷口開闊,行不足二十分鐘即到谷中心平坦寬闊之處。箕形的山谷底部是大山面陰的陡坡,坡上植被以柏居多,間有叫不出名的它樹雜叢,平而略帶斜坡的谷心腹地不足十畝。

踏著雜草踏著未融盡的殘雪,腳下不時被錯綜的荊棘相纏相絆,踩在地上的殘雪,腳下即發(fā)出“咯吧咯吧”的響聲。當年眾多茂盛的槐樹己不復(fù)存在,但仍有高約一人,桿如人臂者,卻也有一二十棵。只是,冬季里,槐樹的葉子已經(jīng)發(fā)黃干枯,葉面也是那種澀澀的皺皺的了。再繼續(xù)走繼續(xù)的觀察,倏地,那毛毛糙糙的條石,并不很長的,非是一根、一根、又是一根,數(shù)了數(shù)約十多根呢。有的沒于土中,只是露了那么一截兒頭,并不在一起,個別的還有上下疊復(fù)的;啊,難道說這就是一千八年多年前槐市人生活、商事遺留至今的佐證么。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作想,既然楊震曾在此講學,那他在此棲身也絕非短暫;進而又想,那就必然有如課堂以及生活的遺跡。只可惜,時日曠遠,我希望見到的那些已無從尋覓了。
噢,忽然拍了拍自己的腦門,人家文管所老師明明說,古槐市在漢代也不過是結(jié)廬而居因人眾而市,看看我這記性!結(jié)廬者,簡單的草房子也。就是今天說的用茅草搭的棚子而己。怪不得建筑遺跡難覓!
恍惚間,似乎隱隱的聽到有朗朗的讀書之聲、商販們的叫賣之聲了。仿佛看到一位面容清矍的儒者,蓄著疏疏朗朗的長髯,著一襲玄色長衫,一手拿著書卷一手反翦背后。心想, 難道這就是老夫子楊震么。
楊震,字伯起,古弘農(nóng)華陰人。自幼聰慧,天賦過人,通曉經(jīng)籍博覽群書,早年曾隨父親楊寶研習《歐陽尚書》,后又師從當時的大儒太常侍桓郁,入仕前隱居華陰的南山,躬耕于壟畝,生活十分節(jié)儉。五十歲后才出山從仕,先后任太仆、太常、東萊太守,后官居太尉。
楊震秉承了楊氏清白傳家的祖訓。為人正直,不屈權(quán)貴。以敢于諫言被譽為諍臣。暮夜卻金的故事流傳至今。他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被人美傳。
東漢中后期,朝庭政治生活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怪圈,后宮干政,宦官結(jié)黨,漢安帝荒于朝務(wù)。楊震不宵與侫宦閹黨同流合污,被以王圣、樊豐為首的奸侫誣陷貶官。在返回故里的路上,楊震覺自己無能,眼見得奸侫專橫朝庭,自己卻不能力換狂瀾。于是,心灰意冷,無顏面見故鄉(xiāng)父老。隨在途中飲鴆而亡。時在安帝延光二年即公元124年。直到公元144年順帝劉保登基之后才平反昭雪。
于是又想,凡歷朝歷代,忠義,正直、清廉之臣大都被誣被陷,下場悲慘?為什么那些奸侫,讒媚,貪腐的官員又能恣意妄為,橫霸朝堂?難道說前者不適天意不順民心么?擬或還是后者有著特別的靠山,就如同《西游記》里的妖魔鬼怪,它們在天庭都有著自己的門路與主子呢?進而又想,難道我華夏氏族從根上就有著這種頑劣的固疾么?一時很難找到合適的答案!
至此,我的思緒又回到了現(xiàn)實。反而覺得背上有些咝咝的涼意。我知道這是上山時的汗?jié)瘢@時才如此的冰冷了呢。看著這空空闃無人跡的古槐遺址,心里不免有一種悲憫和一種喟然。唉,昔時賢人今安在,唯留槐市舊遺跡啊!
臨了。要告別古槐市的時候,我不由自主的向這茅草橫生的空谷鞠了三躬。心里很虔很誠很是敬畏!
出谷,滿身的泥滿身的荊棘小剌與柴草碎葉。然,尋訪了古槐市,拜謁了先賢,雖說對古人古事有所悲憫,但心頭卻多少有一點點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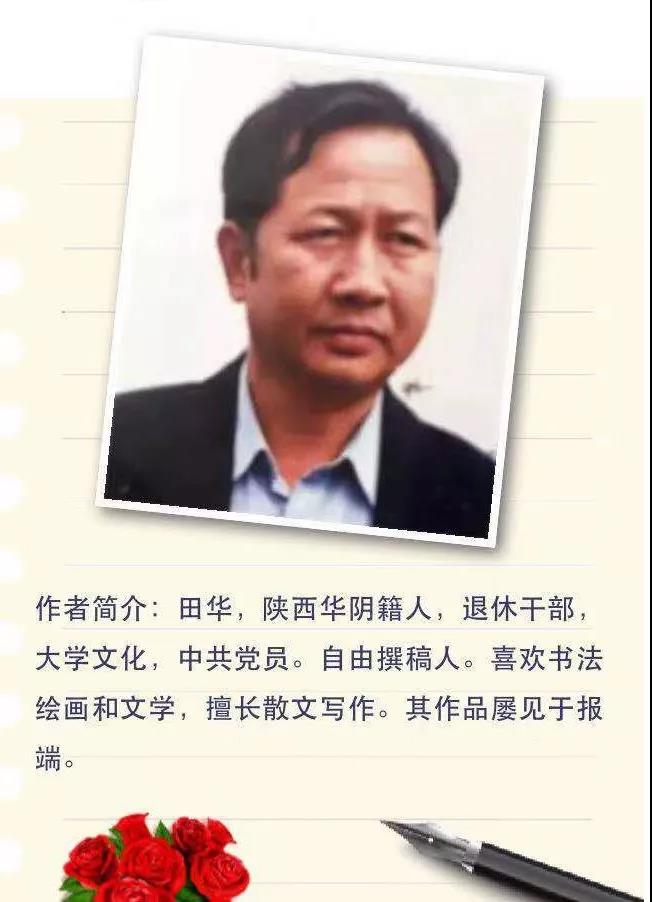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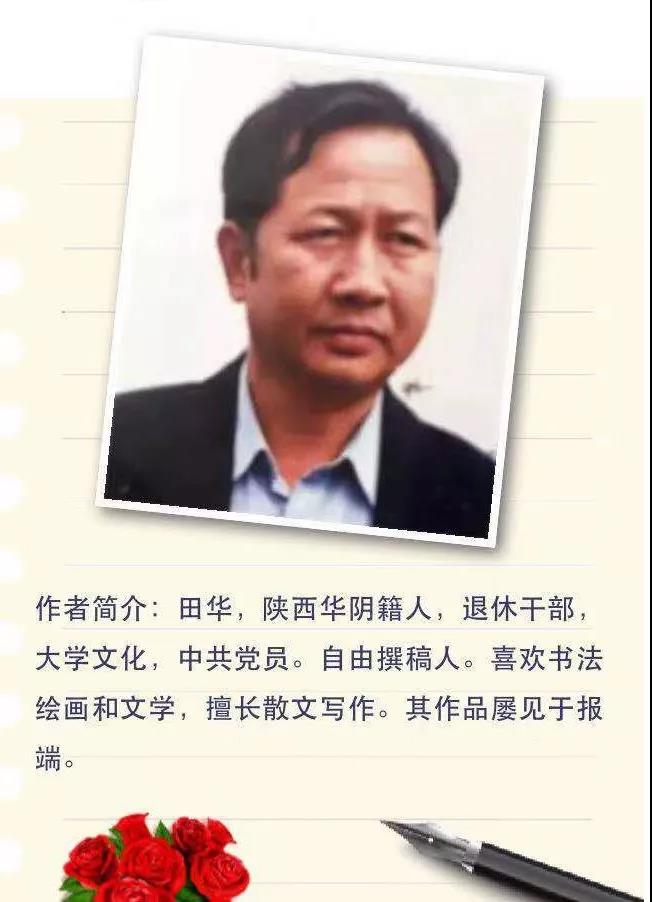



 位客人
位客人